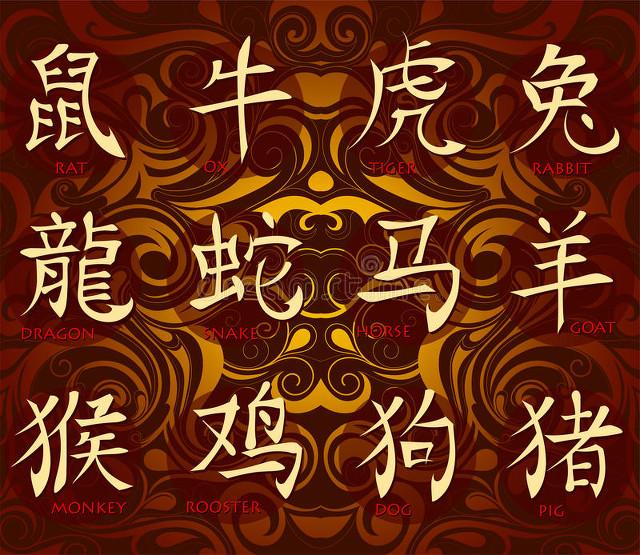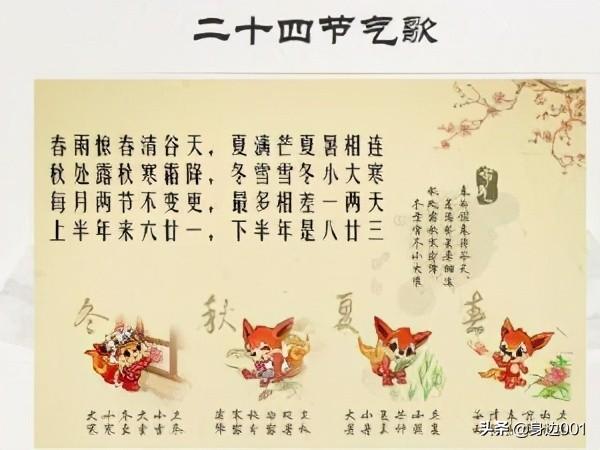评论家张莉编选的2024年女性小说年选《平静的海》,以“爱”“秘密”“远方”为辑,收录2024年度20位不同代际中国女性作家的小说佳作,聚焦女性视角,丰富了文学表达的维度。女性对理想化伴侣的由仰望到“平视”,单身母亲与儿子之间亲情关系的紧张和不确定性,相依为命、彼此为镜的东亚母女之间难以言说的间隙……
编选团队成员从中看到现代女性在情感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变化,以及她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生活轨迹中寻找自我与认同,也看到新的女性话语生成的可能。

主持人:
程舒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方向2024级博士研究生
与谈人:
张凌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方向2024级博士研究生
万小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2023级硕士研究生
吴韩林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方向2024级硕士研究生
她们的“新”故事
程舒颖:第一个话题是,今年选出的女性小说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趋势?这些作品中是否有新的元素和趋势在悄然涌现?
万小川:我想用“打破边界”这个词来概括2024年的中国女性小说。这既是说对传统写作规范的挑战,也是观察力和想象力的超脱。从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到神秘诡谲的叙事迷局,从思绪漫漶的意识流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碎片化叙事,女作家们探索了叙事技巧的多样性,丰富了文学表达的维度。在题材方面,既有直面身体感受和自我内心的勇气之作,也有剖析亲密关系的解牛小刀;有俯瞰时代征候的深刻洞察,也不乏想象力飞驰的未来科幻。女作家们以独特的性别视角观照身体、人性、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了观察世界的多元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传达出破界的勇气和力量。
吴韩林:我发现不少作家对于笔下的女性角色拥有一份非常深厚的理解之同情。这些人物在进入小说时似乎总处在一种“欠然”的状态,而小说想要处理的核心,就是如何与这种“欠然”达成和解。经由作家个体生命经验的融入,这种“欠然”的征候可以超越两性关系的局限,进而指向作家对于现代社会中人情人性的深刻理解。
张凌岚:2024年的中国女性小说似乎比此前更加靠近“现实主义”,由聚焦家庭内部转变为书写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和遭逢。女性视角的挺拔将在某个人物身上的特定故事变成芸芸众生的共生实践,令现实世界在女性视角下暗潮涌动,意义丛生。

“爱”:情感与关系的镜子
程舒颖:收入的这20部作品仍然分为“爱”“秘密”“远方”三个部分,我们首先进入“爱”的领域。这一辑的作品大多聚焦在情感与关系的书写上,探索了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仿佛经过许多面镜子,折射出各种关系的复杂性。那么,在这一部分的小说里,是否有某处情感描写让你耳目一新?比如哪些打破了传统的爱情叙事,又有哪些是在普通的生活细节中掀起层层涟漪?
关于情感与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叶弥的《许多树》。这篇小说关注的是时间如何在情感关系中凿下深深的印痕。叶弥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汪海英对青年时期理想化感情的追忆,伴随她度过了漫长岁月,但在四十年后的现实中,汪海英终于对雷兴东进行了“平视”,把他身上所呈现的生活的琐碎与理想的破灭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并非悲剧,因为背后有一个新的自我正等待她生成。
另一篇是艾玛的《平静的海》。小说从日常细节中挖掘亲情的紧张与不确定性,从一位独身中年母亲的视角来看待她与留学归来的儿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母亲对儿子忧虑重重,一个刚毕业归国的年轻人,卷入了一起失踪案的调查。更重要的是,两人虽同处一个空间,却因为彼此内心的疏离,始终无法真正对话。小说的最后,鲸鱼的意象是对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下涌动的揭示。亲情在这里并非温暖动人,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经历的那样,带着缺憾却又无法割舍,像海水一般咸涩。
万小川:先谈谈徐小斌的《隐秘碎片》。在创作谈中,作者说这篇小说的写法受到了英剧《九号秘事》的启发,通过颠覆性的结尾营造出一种荒诞感。例如,作者细腻地刻画了女演员伍伍在跟名导约会时的欲擒故纵的复杂心态,被名导删了微信的转折便显得格外滑稽;实实年轻时负气出走,得意洋洋,却在多年后得知男人早已再婚,才想起来二人办过一次假离婚。这些荒诞的反转让人发笑,但细想之下,又能从中看到许多现实的影子。作者也许想借此写出情感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小说中看似荒诞、魔幻的情节,往往又映照出现实和常理。
蒋在的《初雪》中,最让我触动的是穆小小和穆芬芳之间的母女关系。作者力图还原一种生活真相:血脉相连的母女之间也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间隙,其中填充着爱、痛苦、矛盾和沉默。穆小小和穆芬芳之间的母女关系如同一块镜子,正面映照出彼此的情感,二人的命运如此相似;背面则掩藏着差别和隔阂。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在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东亚母女。评论区充斥着这些关键词:依恋、争斗、疏离、共振……像一场安静又纷纷扬扬的初雪。
张凌岚:在“爱”的专辑里,二湘《心的形状》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篇小说。作者对当下社会原子化个体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包括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关爱、相互理解并彼此救赎。文中不断提到的“心的形状”其实是对超世俗的直抵灵魂深处的爱与精神共鸣的追求,它虽扎根于现实情欲,其实质却远在生活的日常性之外。
如果说其他小说大都从正面探讨“爱”这一主题,那么王海雪的《白日月光》则聚焦于爱的背面。它如同一面碎裂的闪着冷光的镜子,折射出爱的痛楚扭曲,以及人心、人性最幽微的部分。这篇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怀揣着巨大的沉默的秘密、巨大的沉默的爱,那些未被开解的情愫日复一日在内心发酵,有的变成了怨恨,有的变成了执迷,有的则在放手一搏之后功亏一篑。爱并没有让人变好,更没有成为救赎,反而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当中。看完忍不住思考,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爱、处理爱?

“秘密”:生活表面下的隐秘角落
程舒颖:聚焦第二辑“秘密”部分。从难以释怀的记忆到无法压抑的欲望,这一部分的作品大多通过女性视角,深入挖掘复杂的心理与情感体验,细致描绘了很多被隐藏在生活表面下的隐秘角落。
万小川:读林那北的《春江水很暖》是一个奇妙的过程。起初,读者或许自以为看破了作者埋藏在文本中的秘密,甚至嘲笑作者的俗套——妻子在手机上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跟小三展开对峙。作者也有意误导读者——小说中的某些对话暗示着这种关系的可能性,随着情节的发展,悬疑却转向了钱权交易。读者的期待受到愚弄,不禁返回去重读整篇小说,便能从前文中发现作者苦心埋下的细腻伏笔。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注意力从“事”转移到“人”,从中发掘一个女人从对丈夫的依附中挣脱出来、明确了自身独立性的成长历程。丹梅的那四刀惊心动魄,是一个女人对憋闷、压抑生活的决绝告别。
庞羽的《一个人的塔吊》是一篇奇诡的小说。初读时,纷繁的思绪、意象和情节扑面而来:从日常生活中的短视频、食材、烂尾楼、塔吊、食堂、课堂,到遥远的行星撞击;从与丈夫、父母的现实互动,到对爱情、时空的哲学思考……这一切都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主人公想象力的喷薄和意识河流的汹涌。作者细腻地描绘了一个怀孕女性的极端敏感的心理状态,无论是感官情绪还是人际关系的体验,抑或是记忆,都异常活跃。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情绪都可能被放大——隐秘的孤独侵蚀着她的内心,就如同塔吊独自矗立在烂尾楼上。
吴韩林:何玉茹的《无事》与辽京的《肾上腺素》有关不同代际内心秘密的书写,或可作某种形式的对读。《无事》中李瑞与刘健儿在京剧唱曲中虽然和谐默契,但背后却潜藏着一段两人年轻时与时代相互错位的遗憾爱情。小说对于人到晚年情感的捕捉尤为细腻,在一曲一调中,尽是道不尽的离别与说不完的伤心事。颇有不同的是,辽京《肾上腺素》的叙述秘密却始终悬置在过山车的最高点,爱的宣言与分手的告白同时降临,变化如同急速运转的飞车,让玩家在最兴奋的同时也最为恐惧。但人生的列车一旦发动,谁又能使其停下呢?因此,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究竟是如何在这篇小说中开始变轨的,对于读者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但也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性,构成我们现代人心灵最真实的写照。
张凌岚:张怡微的小说《看见盐柱的寻常一天》也许更能激发我的探索欲,因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我们身处的高校。小说中,林妮通过“学术工作坊”的讨论试图建立起自己理想中的乌托邦。一方面想要触碰切记的现实与未来,但另一方面又在身体与情感的病症中沉湎过去,以至最终只能化为寓言中凝固的一颗盐柱。作者以一种“共情”的方式将学术乌托邦日益凋敝的暗潮涌动拓展开来,既写出了学术从业者仍然抱持的意志理念,又写出了他们被无形的权力机制裹挟和支配的卑弱。

“远方”:寻觅新世界
程舒颖:“远方”这一辑的作品,往往带有探索与寻觅的意味,无论是地理上的远方,还是心灵上的距离,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小说不仅让我们看到新的世界,也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切实的生活质感与肌理。那么,在这一部分的小说中,是否有给你带来新的创作视野的思考?这些作品呈现了怎样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张凌岚:马金莲《踩云彩的大脚板》写出了“远方”的心理距离:对于孩童来说,远方也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远——离开父母的庇护后,连从村小到家里的路都是远的。阿蛋的父母为了谋生,去了县城,在年幼的阿蛋看来,“远方”并不令人神往,反而意味着剥夺与分离。但小说的色调却并不低回和沉重,恰恰相反,当阿蛋率领伙伴们在乡间道路上拔足狂奔,童年的孤独和快活都被云轻轻托住了,一切都显得那样清新而明朗,连心底的自我鼓劲都是那么真挚,没有一点掺假。
而汤成难的《行行重行行》是其“远方”叙事的延续,小说书写了一位沉默的农民父亲对“路”的痴迷和执着,通过叙写父亲在现实里的一次次远行和“我”因结巴而“失语”又因父亲从远方带回的毛笔重新在精神世界抵达远方,诗性而从容地展现了小人物的在表面生活背后的“日常神性”。汤成难在小说中这样写道:“不管哪一条路似乎都能引领人们快速走到终点”,在我们的阅读传统里,“路”是一个坚定指向“远方”的意象,这篇小说通过若隐若现的寓言式写作,将“远方”在异化的当代社会重新锚定在精神世界无限辽阔的纬度上来,人性不屈的微光就这样将我们由此时此地渡至彼刻远方。
程舒颖:提到“远方”,我想到的是须一瓜的《邮差藤小玉》,这篇小说让人感受到“远方”并非是地理概念,而是对希望的内在追寻。当邮差成为了一个时代落后的象征,当妻子心中他所代表的远方不再遥远,藤小玉只能不再将工作视为单纯的运送,而试图以情感的温度和个人的坚守对抗时间。小说中藤小玉讲给女儿的故事“不死草”,也成为重要意象,开拓了文本中的另一重空间。“远方”并非地图上的某处,而是在平凡中寻求意义。
胡诗杨的《土地的飞行》以情动人,以生动的上海地域文化为背景。“我”外婆赵嫦娥内心始终怀揣着飞翔的念头,尽管她生活的土地与她心中“远方”的理想并不契合。周围人无法理解她,但正是这种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内心追求,使赵嫦娥的形象显得异常鲜明与动人。在传统与刻板印象的束缚之外,她以一种纯粹而不妥协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对自我理想的追求与坚持,最终,飞机上的赵嫦娥是否抵达了她心中的“远方”?答案已经随着小说娓娓道来,留在了每个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