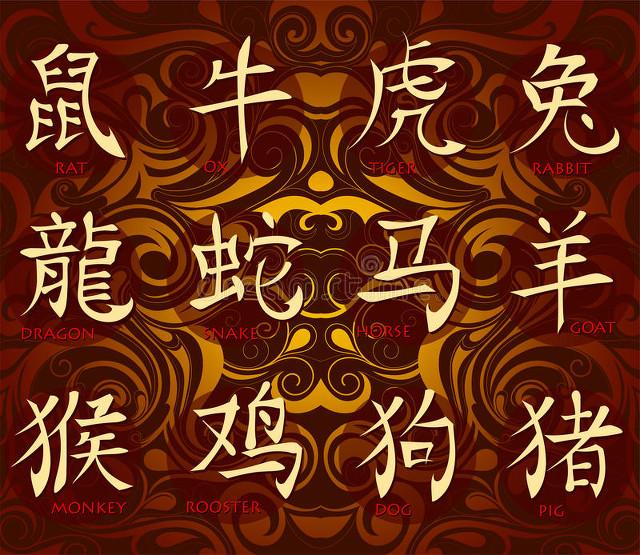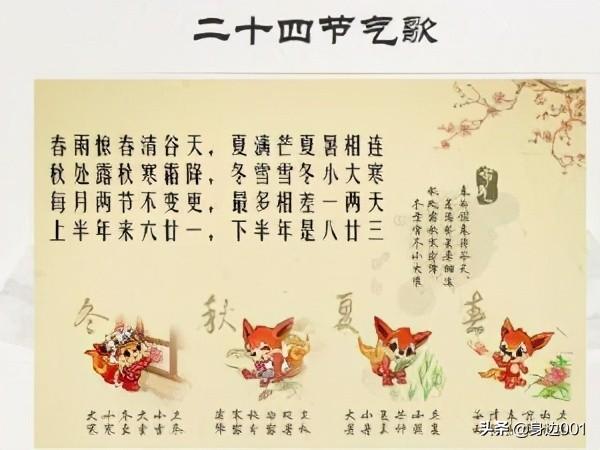“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是艾青在1937年创作的一首新诗。在风雨如晦的时刻,诗人蘸着血泪写下了这首沉郁顿挫的时代悲歌。

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我爱这土地》,郭沫若的《中国妇女抗敌歌》,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光未然的《黄河颂》……在历史时空中声声传诵的诗歌,如今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被艺术家们重新演绎。

当徐悲鸿笔下的雄狮在《会师东京》中昂首怒吼,当《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画面直击人心,当油画《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与杨洪基先生的朗诵交相辉映,这场“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正以诗画为媒介,将我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三百多件美术作品与抗战诗歌在中国美术馆里共振,让“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赤子情怀,在今天迸发出震撼心灵的力量。

馆长导赏画作,文学家读解诗意
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带领我们观看多幅画作。美术作品不止是艺术本身,更是对历史的深刻记载。画作《义勇军进行曲》的主色调,让作家李敬泽想到1938年民族危亡之际创作的《我爱这土地》,艾青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熔铸为泣血之作。这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抗战最艰难时刻,中国人心头的共同呐喊。

从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诗人吉狄马加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当年光未然是在黄河咆哮声中构思出了《黄河大合唱》组诗。抵达延安后,他一气呵成完成创作,冼星海为之谱曲,最终成就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时代强音。这组诞生于战火中的诗篇,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中国素有“以诗言志”的传统,抗战时期的诗人们运用直白、精炼的语言,让诗歌真正走进百姓,吹响战斗的号角。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以破碎隐喻山河的沦陷,陈辉的《为祖国而歌》,用铿锵的节奏唤醒爱国的力量,实现了诗歌“大众性”与“民族性”的完美统一。

评论家的思考与学者的发现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最关注“巴掌大”的版画作品,那是历史的刀锋在时代中留下的真实印痕。在这位美术评论家眼中,版画是历史的“插图”,留下的是一个个经典的意象。在特殊的年代,版画以“顷刻能办”的速度,走进最广泛的人群之中。

诗情画意中也有当代科技力量的硬核发现,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副教授文少卿这次也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他在以诗歌和美术为主题的谈话中,再次印证了团队研究的意义:以DNA(脱氧核糖核酸)鉴定,帮助无名烈士找回姓名与家人;以体质人类学分析,揭示烈士的遭遇——冷冰冰的术语“眶上筛变”显示的,是年轻战士在牺牲前长期营养不良的身体状况。那些嵌进骨头的弹片,让诗句中铮铮“铁”骨的描述成为现实。这次,文教授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他们用科技手段,帮助崔海治烈士寻亲成功。而《战士》诗歌,则真实还原了这名烈士的生命征程。

文老师说,艺术是“信息的压缩”,可以在有限空间内传递磅礴的力量;而科技是“解历史的压缩包”,通过对遗骸进行分析,将凝固的历史细节还原为鲜活的生命故事。二者殊途同归:艺术以升华的精神鼓舞当时的人,科技以真相给我们以精神的力量。
当青年观众在画作前驻足沉思,朗诵诗人们写作的抗战诗歌时,这场美术与诗歌的对话已超越普通的展览。它让80年前的“时代鼓角”传到了今天——抗战诗歌与美术,不仅是历史文献与艺术珍品,更是流动的精神基因。它们在提醒我们:唯有铭记“雪落在中国土地上”的苦痛,才能守护“和平颂”中的愿景;唯有传承“我爱这土地”的深沉,方能让英灵梦中的“诗情画意”照进现实。(文/马宁)